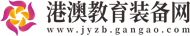【猎杀对决】鳄鱼之泪·间一(爬行动物) 环球微头条
托更了许久,距离上次发作品已经有快九个月了。最近都在忙着升学,实在过于繁忙,对此感到非常抱歉。这次也是憋了很久,最终导致笔法都变得生疏,最后花了很多心思才终于找回一些感觉。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资料图】
【资料图】
上一章的传送门:
本章长度共8442字,如果喜欢,请耐心看完,作者在这里感谢各位了 QAQ
基思·考恩时常在记忆里翻找出零碎的片段。雨后沾湿的暗巷小道,路边行人的张口高喊,酒同汗液的尖酸异味,屋檐上滑落的水滴,深夜亮堂的警局,远处铁轨的轰鸣,懒散的住民,连片的房屋,与那条两英里外蜿蜒的溪流。以前的事物与现在并无太大不同,只是人已经开始更替,房屋上留下些时间的污垢。但这一切都与他没什么关系,因为这片土地于他而言,除开某些不愿去回想的事物外,远不值得去铭记,于是便一点点淡忘了,仅此而已。男人就如同自己青年时的那般一样,只身一人在正午的街道上缓缓的走,节奏的步子沉而闷,犹如乡间时而闻见的马蹄。也如同青年时一样,另一人则是在身后远远的跟。男人回过头,正巧对上那对年轻而又飘离的眸子。看着女孩的脸,不经有些晃神。
身后的人怔住,接着便闻轻弱发问。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他刚想张口,却欲言又止,摇摇头。
“不,没什么。你是叫艾拉,对么......。”
那一刻,他转过身,呼了口气,曲下膝盖,与女孩平视的同时伸出右手,尝试着挤出尽可能和善的笑。女孩眨巴着琥珀色的眼,有些犹豫退缩,指尖微微颤动,但最后还是未能握上那副比她大很多的手。她张着嘴,好久才回道:
“......还请多关照。”
这孩子简直跟她一模一样。他想着,心中涌起一阵苦楚。她当时是否也是这副神情,热情?抑或是退缩?甚至是恐惧?可惜,想浑浊的泥水中寻找细碎的踪迹即便是对于他,还是过于艰难。
他抽回未能触到东西的手,微微昂起下巴,被头顶的明媚阳光扎的睁不开眼,他正了正头顶破旧的棕黑色牛仔帽,脸上笼罩的阴影被趁机剥开些许,可依旧稠厚。
不过他还依稀记得,那日的太阳,似乎也热烈似火。
两人一前一后在镇里兜兜转转,最终停在马路旁的一所店前,悬挂的招牌上雕着硕大的店名。棕色木台阶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门框上垂吊的乌黑煤油灯吱呀吱呀的叫,边响边摆。基思先一步踏进去,宽大的手掌推开店门,迎面而来的便是一股浓烈的劣质油味。房子里的空间不大,暖黄色的涂料中包裹着一丝绿意。艾拉扭头看了看,十步开外有一个向上的楼梯,四周摆满的皆是令郎满目的杂货,从钓鱼的鱼饵到各种颜色的弹药盒,物品很是齐全。她看着他用指节重扣几下身侧的台面,声音就像是木槌敲击般闷钝。大约半分钟后,柜台后左侧的隔间里传来一声吆喝,随即开始响起紧凑的脚步,愈来愈近,直至一名留着小胡子的年轻男人最终从小木门后探出脑袋。他一边用食指和中指捻起根卷烟,边往瘦弱得如同树枝般的躯干上套了件棕灰色的大衣,开口说着,眨了眨绿豆似的眼。
“您要些什么?‘史蒂文森杂货铺’应有尽有。”
“三盒鹿弹,两盒步枪中空弹,绷带,再来点炸药。”
“好的先生,鹿弹,中空弹,绷带……炸药您要一捆还是?”
“中束。”
“了解了先生……看您是新面孔就帮您划个整,那么一共十五美元。”
“还有,再开个房间,要最好的。”
瘦子忽似木棍般杵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神四处飘离,大约十秒后最终才又落回桌面:
“房间……真不巧先生,您或许知道的,这儿附近一直闹匪闹得……很是厉害。”
“所以呢?”
“所以……我们早就不做旅店啦。如您所见,现在这儿是一间杂货铺……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劫匪就把这整个镇弄得乌烟瘴气,现在好了,这破情况弄得连哪怕一头下水沟里的耗子都捞不到油。所有掌权的都不靠谱,包括那个新来的法官,姓什么罗斯,居然还是个女人,我从来就没听过有女人当法官的事情!在这连自个儿家都不安全的鬼地方,谁还会愿意住旅店?”
“你们的警长不管管么?”
瘦子深叹口气,对着上头白了一眼,说:
“警长?你说那个多米·桑德莱?咱们本都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点什么真正的改变呢,结果到半个月前不知道发生什么,跟丢了魂似的什么都不管,有时候人都找不着。现在那群马匪照样吃喝,夺东西抢女人,就在昨天,老雷夫家的女儿都被强掳……!”
兴许是说话太激动,瘦子忽然猛地咳嗽起来。枯瘦的胸膛剧烈地起伏,平缓下来的喘气后紧接着的又是叹息。
“算了……从一开始也就没期待过这些只想着保全自己的畜生做些什么,密尔顿镇的人不需要他们。什么警长,什么法官,什么总统,全都是骗子,毫不关心我们死活的骗子。好人一直被压迫,而坏人永远逍遥法外。总有一天我们也能不必再攀附这些无能的政客,靠着自己活下去……”
他一边在嘴上接着碎碎的抱怨,手在柜台旁的红色大皮包里捣鼓了一会,很快便从一板银白色的烟盒里抽出一根卷烟,随后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递过去。
“抱歉先生,刚才失态了。您或许会想来一根?请您收下吧,就算做我微不足道的歉意。”
“你知道的,我来这儿绝不是为了买点杂货和抽根烟。”
“是,但……先生您知道住在这有多危险。我绝非能保证您和您女儿安全的人,像我这种普通人自保都难嘞。况且这金额住个破旅店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您从这里出了镇,沿着那条最蜿蜒的土路往南边走个几英里就会到格雷镇,那儿比这里可安全了不知道多少倍嘞,我来为您指个路吧。”
瘦子说着,急忙俯下身从柜台下抽出卷牛皮纸,铺开后便成了一张有些年代的地图。他用粗糙发白的手尖四处比划起来,滔滔不绝的为他们讲解,动作很是精细谨慎,每次标划位置都对着身侧的小指南针反复确认了数次,仿佛生怕自己指错了地方。
“我们必须呆在这里。”
瘦子的头忽然昂起来,停在空中愣了一下,心中像是在想些什么,视线往地图上扫了起来,最后终于在某个地方缓缓停下。片刻后,他几乎是小心翼翼的问着对方:
“先生,你们……是之后要去什么地方么?”
话音刚落,那只宽大的手像一头铜斑蛇般轻缓地向前伸去,泛黄的卷烟便被从桌上抓起。男人静静将它衔在嘴里,拍了拍瘦子的肩。
“……”
“先生小姐,祝您们好运,我能帮得只有这么多。我父亲说过,对待要去那里的人……都须好些。既然如此,我也不好再推脱,房间我会想办法,租金也不要了。”
瘦子咽了口唾沫,瞥瞥他帽檐下的疤痕,又看看身旁的女孩:
“只是我很好奇,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这儿以前是旅馆?难不成您是本地人?”
他磨了磨牙,没再言语。
不足一首歌的时间,房间便被很快得打理好了,两人入驻之时,时间正好是下午两点,天空中飘着几朵稀稀拉拉的云彩。艾拉向内探,发现这里的确不差:床大的足以睡下两人,被单洁净,枕头是朱红色,谈谈的木料味让无人的房间也显得温存。房间里无论是换衣镜,储物箱,还是各种颜色的窗帘与装饰都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个位置极好的朝向南方的阳台。随着钥匙被递过,瘦子缓缓交代说这间曾经是他父亲所住,但在他过世后就再也没开过。其他较为次级一些的的房间都已经被用作杂物室存放成箱的货物,短时间内难以收拾出来,因此也只能住在这里,没了其他办法。说完后,瘦子便也没做过多的停留,径直带上门出了去。
坐在床垫上的女孩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
“房间还不错吧?”
然后是混杂了几丝慌张的回答:
“啊……嗯。这里我很喜欢。就是能否给些钱让我去买些换洗衣物,出来时没预料到。”
“当然,待会就把钱给你,自己去买吧。”
“……好的,谢谢。”
空气又再一次沉静,是完全又彻底的沉默,如同齿轮间卡满沙石的时钟。基思翘着腿坐在床对面的木凳上,手中拿着手掌大小的抹布,擦拭着手枪桃木握把上黏着的汗与灰,但没一会视线又飘到女孩被热得有些发红的脸颊上。怕生的姑娘只得低着头坐在柔软的床垫上,为了排解压力而揉起毫无不适的手心。
大约就这样过了五分钟,男人才再开了口。这次,他的语气不同以往,显得有些飘忽。
“蕾贝卡·麦克沃斯,她是你的母亲?”
她不知该去说些什么好,于是只是简短的“嗯”了一声,而基思看了她好一会,才轻点了点头,像是低语般,说:
“你们过的还好么?”
她稍微组织了下语言后,缓缓地说:
“……在母亲走前,多米叔叔也经常来帮忙,生活过的都很顺利。母亲每天都在为了生活操劳,却从来没有忽视过我的感受。我很想她,她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
“是的,生活的苦痛挫不倒她。”
艾拉的头微微抬了些许,尽管在两人眼神第一次交错时她有些显得应激,再次极快得偏过头,但在努力下最终还是调整好了说话的语调。
“考恩先生您……以前认识母亲她?”
“…算是吧,稍微发生过一些称不上愉快的故事,我和蕾贝卡勉强称得上……熟人,不过也不再重要。”
听到这里,艾拉心中原本在许久以前压抑下去的那股情感又再次萌芽似的冒了出来。母亲在曾经就几乎从未提到过自己的过去,但从与她日常相处时的眉宇与神情中所隐隐透露的来看,发生过的定不是什么无关痛痒的小事。母亲——或者说是蕾贝卡·麦克沃斯——既然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那她对母亲的了解已然没法通过与她的相处增加哪怕一分。可那毕竟是养育她抚养她的亲生母亲,而身为女儿的她绝对有权力,也有义务去了解母亲的过去,如果有什么尘蒙的冤屈或者未尽的遗愿,那便更是如此。她联想到她那缺失的不负责任的父亲,就是他抛下她们母女两人自己离开。如果能够找到他,她一定要为母亲讨回一个公道,并让那个有名无实的父亲有所偿还。
她这次便没在去躲闪眼神接触,而是一反常态得直勾勾得看着他,这也让不明女孩心中所想的男人挑高了几分那对浓厚的眉毛。
一定要为母亲讨回公道,他一定会知道些什么。她如是想到。
“怎么了艾拉,有什么事么?”
“是的考恩先生,我有问题……想要问问您。”
男人如同往常般回笑着,说道:
“说吧。”
“母亲以前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我想知道。”
“我并不清楚那些,恐怕帮不到你。”
“……多米叔叔跟我说过的,说你知道些什么,让我自己问你。”
她并不擅长说谎。在言说这一句话语时,她自己都能感受到声音中因为慌乱而导致的颤抖。可话音未落,对方的笑容已然突然凝滞,嘴一张一合像是只搁浅的河蚌,似乎毫无精力来辨别这个蹩脚谎言的真伪。他尝试开口说些什么,却又被活活如同生吃昆虫般艰难地吞回去反刍了三遍,第四遍时口中的卷烟如同秋后落叶般“踏”得落在黄褐色的橡木地板上。男人咬着牙一把将其再次拾至唇前,点燃,深吸,刺鼻的气味充斥起整个房间,窗外射进的光线在灰白烟雾的掩盖下忽明忽暗。
“我刚才说过,那些事都不重要,你无须了解。”
“所以您不否认您跟母亲的事情了,是吗?”
他呆住,半拍后旁边的小木桌被狠砸一下,那满含怒意的咒骂中毫不避讳的反复提到警长的名字。
“请您告诉我吧,我真的需要知道。”
“……年代久远我已经有些记不清了,我没法告诉你。”
“没关系的我可以慢慢等您,无论多久都行!”
“我现在不想谈论这……”
“考恩先生,我是她的亲生女儿!母亲她现在走了,我已经没法与她再说上一句话了。您不愿意说,多米叔叔也不愿意说,那我还应该从哪里去对她有更多的了解!我答应您不会去造成任何麻烦,只是想要听到真相!”
“……”
“或者说您知道我父亲的事情吗!”
“……”
“他背叛了我的母亲,我必须找到他!”
未谙世事的女孩在此刻全然涨红了脸。
艾拉从没跟人如此激动的说过话,但她仍能感觉到自己脑中有某种奇异的兴奋感在冲击着她,也仿佛感觉自己无比渴求的真相也近在咫尺。随着那具纤细的女性躯体愈发向着男人的方向前倾,她愈来愈坚信只要再多询问一下,他一定会如同口含珍珠的蚌般吐露出她想知道的一切。
“别说了!”
这是一声炸响。
女孩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
直到房间里已然烟雾散尽,窗外新鲜的泥土味再一次扑面而来,野雀的鸣啼再一次清晰可见,男人才忽然毫无征兆地站了起来。
她鼓起勇气抬头看去,看着他从钱夹里抽出一小叠钞票,揣进兜里,然后径直向外走去。推开门的那一刻,艾拉对上得只有闷钝的脚步与宽大的背影。
我向你道歉,我失态了。他说。但我现在得去处理点事。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休息,晚些还要再出趟门。钱放在凳子上,全部给你,不够再找我要。
他并没有回望,“砰”地一下,很重地带上了门。
门外热气滚滚,但手心仍旧无法克制得感到一股恶寒。
待脚步完全远去后,艾拉才缓过神来,终于伸出手拿起了那可以说的上沉甸甸的皮革钱夹,她用手指撑开一看,发觉里面的纸币多的令人咋舌。女孩将那毫不夸张,可以说是厚成一沓的钞票拿来仔细点了足足四遍,才最终确认自己并没有弄错任何东西。
钱夹里塞了足足一百八十六美金的纸币,难以计数的零钱,与一张德克萨斯州州立银行的三千美金支票。
面对如此巨额的钱款,年轻的女孩脑中想的不是男人究竟是如何活得如此阔绰,亦非如何挥霍它们,而是一片空白。
过了片刻,白皙的指尖还是没能从夹中抽出纸币,她不再思考,仰躺在床,合上了眼。楼下瘦子隐约的吼声中,女孩眼前再次映起母亲的面庞,。
TIPS:在故事背景的二十世纪初,一名美国普通工人的年薪在三百美金至五百美金左右。一支名牌工厂生产的枪支价格大概在五美金到十美金左右。
“滚!这个烂杂货铺接待不起你们这些高官!是我们不配!”
是瘦子的怒骂声。
“先生,您别这样,我真的只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是女人的恳求声。
“跟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天天整些投票,意见什么的,到头来你们真正管过什么!一个个的收了些破钱贿赂就开心的不行,简直让我想吐!”
“我才刚刚上任,但我保证会改善……”
“我什么我!‘尊敬’的罗斯法官,你告诉我,你这个新来的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改善?难道这周围的暴行不该改善吗?老雷夫家的女儿被当着老雷夫的面拖走,约尔逊的儿子见义勇为结果当街脑袋被开了个洞,还有我那被谋杀的父亲!况且连男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你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完成……真是该死,这样下去这个地方要玩完了……算了,我不想和女人吵架,滚吧。”
瘦子口中满是厌恶。
“抱歉先生,是我不识趣,打扰了。我对您的遭遇感到非常抱歉,即使您不待见我也没关系,我仍然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做出改变,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话语绝非虚伪。您的意见对我帮助很大,所以,祝您……今日愉快。”
女人口中满是疲惫。
基思走上回杂货铺的路已是日暮时分。余温仍在街坊之间流窜,而骄阳早已变为一盏悬于天边的橘黄暖灯。这地方的的确确的变了,他心想。小时候,砖墙上的涂料从没如现在这般饱满过,人们饥肠辘辘的肚子也是。城镇,或许真的成了一个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但这里终究不是自己的归宿。究竟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应该逃到哪里去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逃不动了。
路过镇中心的时候,他无意间瞥见镇中心那具老旧的绞刑架。吊木已经开始朽烂,麻绳于风中摇晃,颗颗风滚草缓缓飘过沙尘大地。绞刑不同于斩首,刑场里见不到明晃晃的利刃与嘶嘶磨刀的刽子手,也嗅不见狼烟般直冲天际的血腥气。只闻鸟啼凄厉,闸一拉,人一落,颈一悬,那便是生命逝去的全部。他浑身触电似的一颤,眼前景色顿时恍惚。他回想起自己的十七岁,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观看绞刑。仍是青年的他便已经听见过许多声音,有脖颈扭断发出的脆响,有人群高声的侮辱和唾弃,有活板拉杆被拽动的摩擦声,但绝不止这些。回忆中谩骂声永远参杂着受刑人的泪与被踢踹后痛苦的闷哼,即使现在,当时沙砾吹上皮肤的刺痛与胸膛中躁动不安的心仍然新鲜如初。可此刻,他好似自己也被粗暴的推上绞架,双手也被拷上沉重的银铐,身下渴求死亡的吼声已然声嘶力竭。
所有人都盼望他的死。
他们都需要一个交代。
就在头伸入绞索的前一刻,他看见的是一名女人满是鲜血的脸。
天边的夕阳在燃烧。
她眼中喷涌着的是漆黑的火。
她眼中喷涌着的是地狱的火。
而面对死亡,他早已流不出泪。
他不知于回忆中沉迷了多久,直至一声呼喊将他拽回现实。
“先生!请您留步!”
这声音是个女性。嗓音不尖不钝,意外的中性,但却满含着亲和力。直到她终于喘着气来到他的跟前,他才终于有机会仔细打量对方一下。这名女人长得不算高,大约五点四英尺左右,身材不算招人眼目,略显稚气的脸上长着几粒雀斑,让人有些猜不准年龄;她反常的身着一件深蓝色,印着灰色条纹的高档男士大衣,内部十分整齐的白衬衣领口上打着淡红的长领结,而胸口的铭牌也被擦拭的一尘不染。基思发觉她的装扮异常接近男性,唯二显得有些许女人气的可能便是那头棕色的波浪发被留到了及腰的长度,以及那下半身的服饰是黑色的女性长裙而并非男士西裤。
她深呼吸了一下,照应晴空的湖蓝眼眸随之仰起。
“请问,现在方便询问您一些问题吗?”
男人的眉头紧锁起来,额前时光留下的皱纹如同刀刻。
“……我认识你吗?”
“抱歉,这是我的疏忽。我是艾琳娜·罗斯,密尔顿镇新上任的当地法官。”
他咋了咋舌。
“法官?一个女人?”
听到“女人”二字,那张脸随即僵住,很不满的模样。
“请问你对女人担任这个职位也有什么意见吗?我先说清楚,我并未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妥。如果你和那些人一样,对我女人的身份意见很大,那我也不浪费时间了。”
“不,很少见罢了。”
对方的眸子眨了几下,舔舔薄薄的嘴唇,身后的远方响起一阵马鸣。
“谢谢……您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好说话不少,我还以为您会和那些人一样……”
“我很乐意接受你的感谢,但还有人在等我。”
“十分抱歉,我现在就开始。”
她说着,从身上灰黑大衣胸前的夹层口袋中抽出钢笔和一本描画着触纹的笔记本,又将本子翻开,熟练的在右边的页眉上记录好日期后又翻到另一页。本子上面的内容密集到令人头疼,端正的字迹书写的近乎有关乎民意的采访问题。尽管如此,这个过程还是很简短,这个过程不到五分钟便结束了,看得出来是特意有刻意进行过优先级筛选和压缩。
“感谢您的配合。”
她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直视男人的眼眸,几粒小小的雀斑随着眼角的笑意一同翘起。就在基思准备转身离开时,中性的女声又叫住了他。
“最后的最后,先生,请问您方便告诉我您的名字吗?”
“乔治·皮特森。”
又一个假名。
“没问题,皮特森先生,我记住您了。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条路走到底右转,如果您有需要还请随时找我,很乐意为您排忧解难。”
他没回话,头也不回的走了。
……罗斯么?
想到这儿,阴影再次于心头缭绕。
“起来吧艾拉。”
门口传来很硬的皮靴踏地声。女孩躺卧于床上的身体忽然绷紧,坐起。一个中年男人直直站着在门框旁,背后挎着几根被麻布条包住的大小不一的棍状物。
“时间不早,待会就要天黑,该走了。”
声音简短的就如同军队里无可反驳的号令,她听得出来,对方已经尽可能地温柔,但两人的距离感仍旧很远,宛如横跨地图的两端。
女孩似乎努力想让自己的神态显出重逢般的欢喜,但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况且刚才还因为自己使他生了气。终究,那股神情还是隐了下去。
“考恩先生,您刚才是去买了什么东西吗?”
男人没回话,从一旁拾起先前自己放下的钱包,看了看:
“倒是你,什么都没去买么?”
她发觉话题被自然的岔开,但或许是由于方才的经历,她不敢再继续追问,唯恐再次惹是生非,只得默许了话题的切换。
“是的……整个人有些累,就睡了一觉,然后……”
“刚才是我情绪太激动了。”他轻轻于床上坐下,与女孩贴近了些,接着又侧视着坐在床上的她,眼中的光变得黯淡几分,“这已经是老毛病,多米以前也经常这么说,但我从没成功改掉……你应该也知道,有些东西就算是成了大人也很难改,就算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其实也不见得有多成熟。论性格方面而言艾拉你绝对胜过我,所以还请原谅我…好吗?”
“不,不是的,刚才您会变成那样我也有错,是我得寸进尺了……”
女孩犹豫了一下,指尖抓进厚厚的棉被,回答的声音几乎微弱:
“是我又梦到母亲了……”
他的眼神飘忽了。
“她和你说了什么?”
“没有……什么都没有……”
“只是看着?”
男人顿时语塞,女孩问:
“您说……母亲会不会是因为讨厌我,所以才不和我说话。”
“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我……母亲她走的时候,我什么忙都没能帮上。而且我从出生起,好像就一直是她的累赘。没了我,她本能活得更好,可以享受更好的人生。我对不起她。”
男人走上前,眼神低垂,用手背蹭了蹭女孩的脸颊,那一声哼笑中满是苦涩。
“她没法有更好的人生绝不是因为你,我向你保证。不如说,或许是因为你的出生,她才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来独自面对所有。”
女孩不明白男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也只能似懂非懂的点点脑袋。她重重吐了气,又说:
“最主要……我哭不出……这是不是因为我不够爱她……”
说完,她抬起头,正巧对上那对漆黑的眸子。
“不是的,你足够爱你的母亲,你母亲也足够爱你。”
“考恩先生,那您的家人离开您的时候,您也没有哭吗?”
“……没错,艾拉,和你一样,我也没有。”
他的笑一直太复杂。她心想。似笑,却不只是笑。可等到她定睛一看时,男人脸颊上不知为何淌下的泪于窗外光线照射下闪着微光。女孩惊讶的呼喊,连忙忙翻出一块手帕,向前伸去尝试擦拭男人的脸,却被对方轻轻挡开。
他吸了口气,说自己的天生泪腺异于常人,情绪一有起伏就会流泪。
“等你再长大些就会明白,眼泪都只是骗子用来博取同情的工具,它永远无法代表什么……人只要想哭,都能哭出来,因为他们有必要在当时的场合这么做,但很多时候他们的心却没疼过一秒。艾拉,那你呢,你心痛吗?”
“……我想,是的,我想她了。”
“那你不就已经得到答案了么?”
他再次站立起来,轻拍女孩的肩,将先前买的弹药和所有杂货都一通塞进背包。
“我们得走了,艾拉。”
“请问我们要去哪里?”
她面露疑色地问。
“一个你母亲会希望你去的地方。”
他毫不犹豫地答。
(如果觉得好看还请点个小小的赞,这是对作者莫大的肯定!欢迎老爷们在评论区提出建议,作者会尽自己所能采纳并学习。)
标签: